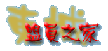中华遗嘱库:珍存父母给子女的“最后留言”
口述 陈凯 撰文 李骐君 郑长宁
感受讲述者
陈凯是一位青年律师,自创建中华遗嘱库之后,他成了老人眼里最受欢迎的年轻人。作为首届北京十佳青年律师、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的心愿就是如何帮助老人解决后顾之忧。在他看来,为老人建立遗嘱库解决的不单单是遗产的继承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将人类的文化、文明一并继承、遗传下来,这些社会人文财富是人类发展的真正财富。
陈凯也给自己写了份遗嘱,留给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他说,那天夜里辗转反侧,于是起身来到书桌前,为自己写下这份遗嘱。这里既有他对人生的看法,也有对孩子的嘱托。他想,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感悟对于孩子是最大的财富,以后他也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修改一次遗嘱,让自己的人生以遗嘱的形式传承下去。
中国人的传统是讳谈死丧,遗嘱也是如此。当陈凯将中华遗嘱库作为他工作的主要部分时,很多朋友都不能理解。但是,陈凯觉得,人们不理解也是人之常情,他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一本旧书带我走上律师路
刚上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差,是班里的倒数。高二时,我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书,书名是《法苑谈往》,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洪丕谟老师写的,讲述的是中国法制史。虽然这本书破破烂烂,但我一直留在身边,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能溜到法律的后花园中去,看到一番别样的风景。那些我们看起来冷冰冰的法律,其实有很多温馨的、有人情味儿的逻辑和道理在里面。
看完那本书,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立志要学法律,做一名律师。在这个志向的驱动下,我的成绩就从倒数变成了高考时的全班第五名。那是1995年,法律是非常热门的专业,我觉得学法律一定要到北京,最后经过综合考虑,就到了北京化工大学,成为那个学校第一届的法律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我的师傅是现在律师界非常知名的蒋勇律师,在他手下工作的那一年多,为我整个职业生涯打下了很深刻的烙印。从那时开始,我一步步“对焦”,接触过公司法务领域、股权并购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涉外领域,代理了一些有影响的案例。我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起委托理财案件胜诉方的代理律师;澳大利亚好几家上市公司在中国的法律事务都由我作全权代表;专利、商标甚至驰名商标的案子我也做过。
在每个领域我都做了很多的尝试之后,我发现,真正没有人关注,而社会又迫切需要,同时各方面建树、研究都很少的就是继承法领域。
我的人生有几个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离我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还差6天,我没能用自己挣的第一笔钱给父亲买一份礼物,是真正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走后,我在事业和生活上遇到困境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得到父亲的指导,其实父亲是一个有能力给我指导的人。父亲去世后,有一次我回老家,碰到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你父亲生病的时候曾经提过,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走后两个儿子会不会太悲伤。”
父亲没有留下遗嘱,导致了我的一个遗憾。我现在给我儿子立的遗嘱,就有我对他的叮嘱和指导,这些指导不一定全面,但都是我的人生感悟,对他来讲可能在某个时候会是很好的安慰。
2007年,我到澳大利亚去工作了几个月,结识了一些当地人,和他们聊到中国。当谈到中国人没有立遗嘱的习惯时,他们都非常不理解,遗嘱对于他们来说是必需的,他们认为有孩子以后就应该写,这是最基本的观念。
回国后,我一直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研究这方面的法律。我陆续接手了一些遗产纠纷案件,这些案子后来有的和解了,有的判决了,但无一不给这些家庭、给几代人留下了非常大的阴影。我想,这些阴影是可以避免的。《继承法》要解决人现实的问题,家庭的和谐问题,财富的传承问题,社会的传承问题,前面的基础性建设必不可少,但目前在现实中这一环节是缺失的,所以我决定策划和推动建立“中华遗嘱库”。
为老年人排解后顾之忧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非常认可我的创想,在他们的共同发起下,2013年3月21日,中华遗嘱库正式运行。第一天开门,门外的老人已经排队到半条街以外。前三天来立遗嘱的老人有七百多个,6部热线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状态。现在回头想想,其实遗嘱库能有这么大反响,不是说遗嘱库本身做了多少工作,而是我们刚好踩在了“有一层浮灰的火山上”,把这层浮灰踢开,才发现下面是一座火山。
筹备过程很顺利,各方面对这件事非常支持。最大的支持来自于民政局、老龄办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北京市工商联、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等单位。现在中华遗嘱库的预约量是4万多份,登记量是7000份到8000份之间。我们免费提供的服务是预约、咨询、登记、保管、发放遗嘱证这五项。在这些环节中,老人自己要承担费用的是精神评估,可以自己去我们指定的4家医院做精神评估,但如果是已经公证或律师见证的遗嘱,就不需要精神评估了。后续他们的子女来查询和提取遗嘱是有一定费用的,但并不高。
在遗嘱库登记的标准流程是:先预约,预约有好几种方式,有电话预约、网络预约、现场预约;排队,等候去现场登记的通知;到达现场后先核验身份;身份核实无误后进行咨询;打印一份遗嘱草稿,在见证人的见证下抄写遗嘱草稿;抄写完成后进行精神评估;精神评估正常后登记遗嘱。最后把遗嘱保管在遗嘱库,得到一本遗嘱证。同时将立订者填写好的遗嘱原件通过扫描成电子版本入库留存,纸质随同保留。得到遗嘱证之前还有一个审核环节,我们要审核工作人员的操作,提供的材料等,这样一份入库遗嘱就算完成了。
在文本保存上我们建了三级库,分别是临时库、中转库和永久库。临时库是从银行租的保险箱,中转库是在顺义的一个仓库,这个仓库做了高等级的改造。永久库我们目前正在筹备,规划是在全国建立三个以上的数据备份中心。
有人担心遗嘱库入库的遗嘱能否保证其真实性,中华遗嘱库是一个公益组织,是独立于诉讼双方的第三方,处于一个超脱地位,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没有任何问题。入库的遗嘱都是经过指纹、问答、扫描和录像的环节过后存入库中的,中华遗嘱库能够证明这份遗嘱是当事人自己签署的,而且反映了立订遗嘱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正常。
前两天有一个第一批登记的老人回来,他上次是自己立遗嘱,这次是和老伴一块儿来立遗嘱。他说:以前我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好,整天辗转反侧,每天就想着到底该怎么办。登记完遗嘱之后,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终于踏实了。老人家给我们送来了锦旗,上面写着“解后顾之忧”五个字,这五个字真是说出了老人们的心声。
当然也有质疑声,有些专家学者认为,立遗嘱是出了问题的家庭才需要的,没出问题的家庭不需要。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出了问题和没出问题,其实都需要遗嘱。没出问题的要有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不能等家里出了问题才去解决。别的事情或许可以亡羊补牢,但遗嘱这件事是没有机会重来的。也有人认为,这个家庭本来好好的,一立遗嘱反而起矛盾了。这是一个逻辑错误,把因果关系弄混了,如果因为老人立遗嘱就闹矛盾,恰恰说明这个家庭本来就有矛盾,这种情况,我相信如果没写遗嘱,老人去世后矛盾会更突出。
遗嘱是家训也是精神财富
在我看来,遗嘱其实是父母给子女的“幸福留言”,人人都应该有遗嘱。遗嘱的延展性很强,在更高级阶段能承载更多的东西。
老人想立遗嘱,可是家里人知道了会闹,这种情况怎么办?这就是遗嘱库的功能——老人的事情老人自己办,办了以后没有义务、也不应该告诉子女。
现在社会,通常老人的财产是自己形成的,子女没有贡献,很多时候,正是子女认为老人的财产是子女的,心态不对才出现矛盾。如果子女认为老人的财产就是老人的,我对你好是我的本分,你给我遗产是你的情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了。很多人觉得我辛辛苦苦赡养了你,你的财产就应该给我,这种心态,早就忘了子女赡养父母与父母养育子女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也早就忘了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
我认为,有家庭、有小孩,就该立遗嘱,这和财产多寡没有太大关系。原因很简单,遗嘱体现的不仅是对财产的安排,更是对家人的爱和关怀。另一个方面,我们比较一下,一个三十多岁的忙忙碌碌的中年人和一个七十多岁整天打打麻将、遛遛弯儿的老年人,到底谁更应该立遗嘱?从对家庭的意义、经济活动的频繁程度、逝世后家庭承受的压力这些角度考虑,显然还是三十多岁的人更应该立遗嘱。
近年来独生子女家庭成为社会主流,很多人认为只有一个孩子,已没有必要立遗嘱。在理念上讲,这是不对的,人对自己的财产应该做出科学的安排,这样能够节约子女继承财富的时间和成本。此外,还有很多风险是父母没意识到的,比如说子女离婚,有可能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的遗产会被分走一半。
纯粹从法律角度讲,遗嘱的主要功能还是分配财产。但站在社会人文的角度,它能起到的功能太多了,它可以是家训、也可以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把几代人的若干份遗嘱放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一棵家庭传承的大树。这个事情的意义现在可以考虑了,我觉得它是中国社会需要的东西。以前在农村有祠堂,在祠堂找得到自己的根,这个根对人来讲就是一个个名字。现在进入城市的人很难找到自己的根,把遗嘱库建设好以后,意味着进入城市的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根。所以我说,我们未来要建成三个库,一个是看得到的遗嘱库,第二个是数据库,第三个就是中国人家庭传承的精神“祠堂”。
天津日报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tjrb/2015-01/15/content_7225381.htm